9月上旬,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锡文率调研组来湖南,就推进国家粮食政策相关改革进行专题调研。
湘声报记者跟随调研组发现,粮食生产从种植到加工、储存等各个环节都有着诸多不易,大家期待通过改革,让农村释放更大活力,粮食安全得以更加稳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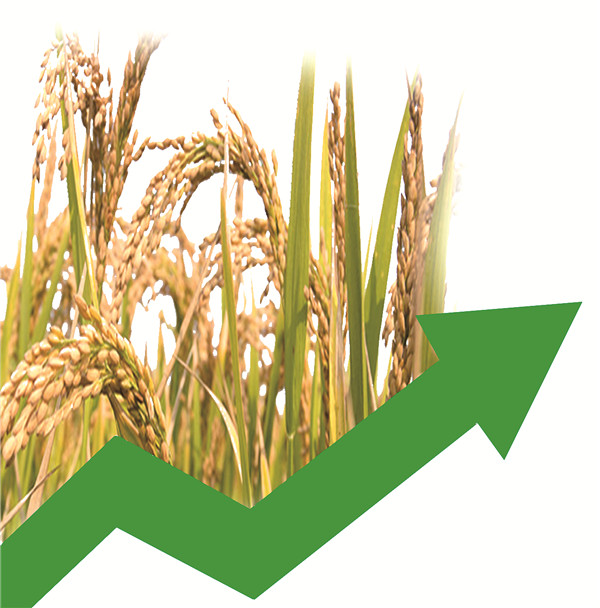
不断上涨的成本
“农民种粮积极性正面临着挑战。”60岁的蒋金华说,各方因素的制约使得种田的人越来越少。
蒋金华是岳阳湘阴县爱民村人,该村有300多户,但在家种田的青壮年劳力(50岁以下)不到30人,基本上都是60岁到70岁的老人,更多村民奔向城市,寻求发展。
“一亩田种双季稻,无论怎样精耕细作也就几百元收入,只相当于两三天的务工收入,并且没有上升空间。”岳阳市农委主任孙志城说,如今,务农的收入已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且比重还在逐渐下降。
留在村里种田人的日子并不轻松,他们要担忧天气,还焦虑着逐渐上涨的生产成本。
作为种粮大户,蒋金华已流转农田2000多亩,让他感受最为明显的是人工成本的高涨。
蒋金华举例说,现在请一个季节性普通用工,男劳力200元/天,女劳力150元/天(天热不超过6个小时),农机操作员400元/天(不超过8小时)。这使得有些村民先不种自家的地,而是给大户去种地,赚取工钱。
担任农副产品成本调查员23年,岳阳县新庄村农民余以新发现,从2005年至2016年,化肥、农药和水费等都在不断上涨,水费和钾镁磷肥则翻了一番。
不断上涨的成本,正挤压着种田者的利润。
为了2万多亩的农田,屈原管理区的种粮大户阳岳球已投入设备1650万元,若每年每亩种植两季水稻,开支约2355元,但每亩收入约2600元,纯利润只有245元。
从2012年开始,岳阳经开区的任术伍从事粮食规模生产,如今种植面积近3000亩,年生产粮食1500吨。“如果只种植早稻,扣除农药化肥、人工等各方成本,每亩利润仅为85元。”
风吹稻浪,站在田间,任术伍时常感慨种田的艰辛与不易,钱也越来越不好赚了。
最低收购价变市场最高价
2004年,为了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国家释放了三大利好政策:实行最低收购价、免除农业税、对农民予以补贴。
此后,国家会在每年农民种粮之前公布一个价格,即最低收购价。调研组组长陈锡文,曾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他说,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是要对市场价格起到托底的作用,不让粮价掉下来。如果市场价格低于最低收购价,即会启动“托市收购”,就按照最低价来收,从而保证农民“卖得出去”粮食。
2004年,早籼稻最低收购价确定为每斤0.7元,中晚籼稻则是0.72元。此后,该价格一直未动,直到2008年,随着土地要素、劳动力等各方面的成本不断上涨,国家才开始上调最低收购价。至2015年,早籼稻每斤的最低收购价增至1.85元,中晚稻每斤1.88元,涨幅均为92%。
“最低收购价很有积极意义。”陈锡文说,政府的价格调控促使国内粮价基本稳定,这既保护了农民的收入,又稳定了国内的粮食产量,从而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
但弊端也开始显现,不断上调的最低收购价,已经不被市场接受,政策性的最低收购价变成了市场最高价。
部分冲击来源于国际市场。2012年以来国际粮价暴跌,几年间全球国际贸易粮价跌掉40%至50%。这也导致近些年国内国际粮价“倒挂”现象成常态。
为此,从2016年起,国家开始下调最低收购价。现在,早籼稻和中晚稻分别为每斤1.3元和1.35元。中央储备粮汨罗直属库主任陈军说,这一价格依旧比市场价格高。以今年早籼稻为例,国家最低收购价为130元/百斤,托市启动前,市场价格仅为125元/百斤。
“如果民企按照最低价收购再加工,则意味着亏损。”省农委副主任刘益平说,由于原粮与产成品价格倒挂,粮食加工企业生产困难,效益持续下降,一批粮食加工企业因此转型或者停产、倒闭。
在汨罗,今年部分规模较大的大米厂经营者已放弃加工,专做粮食贸易,在收购粮食后,再卖给中央储备粮汨罗直属库。
“正常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应该是供需关系的真实反映。”陈军说,当前的最低收购价远远高出了市场价格,对市场的供求信息产生了较大误导,市场又不具备对最低收购价的矫正能力,从而导致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紊乱。
在中粮米业(岳阳)有限公司总经理卢其桧看来,这由此导致了一个尴尬的局面:一边是粮食进口量年年创纪录,优质粮油需求远未得到满足,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越来越小;另外一边是国内连年的粮食大丰收,库存爆满,库存粮食难以消化。
大量粮食无法推向市场
作为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的主体,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储粮)如今俨然成为了粮食市场的“巨无霸”。
1990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制度的决定》,开始在全国建立起历史上数量最大、管理严格、调得动、用得上的粮食储备体系。
当年成立了国家粮食储备局,但这时粮食都由地方粮站收储,使得储备粮经营很容易受地方利益影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央决定建立中央储备粮垂直管理体系。2000年,国务院决定对粮食流通体制进一步改革,并成立了中储粮。
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之后,随着粮食产量的逐年递增,中储粮的收购量也逐年增加。仅2016年,中储粮总公司粮食购销总量达2.43亿吨。
但大量的粮食却无法推向市场。以中央储备粮常德直属库为例,目前该库库存达100万吨,其中2013年产的粮食仍存有1.5万吨,2014年产的粮食仍有14.3万吨。
陈军说,由于顺价拍卖,市场无法接受,去库存进度缓慢,而每年托市粮仍保持高位,形成“进的多、出的少、储存难”的堰塞湖现象。为此,国家需要对中储粮进行大量补贴。
“中储粮在我省除在常德有2个直属库外,其他地市仅有1个,根本无法做到全面收购。尽管明确了委托收储库点,但委托补点不合理。”常德市副市长龚德汉说。
由此,出现了部分粮农卖粮难的问题。调研过程中,多位种粮大户反映,许多村民时常送一车谷到粮库时,碰到的是长长的队伍,等三五天才能将手中的粮卖出去。
面对租车难、运费贵、耗时等问题,许多种粮户最终不得不将粮食以低于“最低价”的价格卖给粮贩子。
湖南成事粮油收储有限公司总经理余文亮认为,若是信誉好、条件符合的民企能够享受中储粮同等待遇,也可做到敞开收购、就地就近收购,方便群众卖粮。
好粮卖不出好价
2017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要“优化产品产业结构,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重点发展优质水稻”。在当前最低收购价格较高的情况下,调优稻谷品种有一定难度。
龚德汉说,按照目前统一制定的最低收购政策预案,不分品种、不分优劣,只按质量等级应收尽收,给种粮者的信号是“只要亩产高就收益高”。
“种植优质稻有一定风险,产量不如常规稻稳定,种子等成本投入又相对普通品种高。”陈军说,在利益的驱使下,农民偏好种高产的常规稻、杂交稻,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被最低收购价格所抑制,不利于优质稻的推广种植。
这也导致了目前粮食种植品种多、乱、杂。据统计,常德稻谷种植品种达到370多个,其中常规稻40个、杂交稻330多个。
湘声报记者发现,一些大米加工企业也曾尝试做中高档米,但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基本勉强维持,有的选择放弃。农民手中有好粮也卖不出好价,种粮积极性受挫。
临湘市召丰水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兵驹认为,统一粮食收购价格看似公正,但对种粮农民来说并不公平。因为不同的农民所拥有的生产资料不同,所处的生产环境和条件不同,成本和效益相差很大。
张兵驹建议,粮食定价在参考国际粮食价格、考虑全国一盘棋的同时,考虑分级收购,实行优质优价收购。
势在必行的改革
为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国家已经吹响了对粮食相关方面改革的号角。
2016年,国家发改委按照“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原则,对东北三省一区玉米收储制度进行改革,将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新机制。今年,国家发改委还调整大豆目标价格政策,实行市场化收购加补贴机制。
这意味着玉米和大豆的价格由市场决定,政府对玉米和大豆生产者给予一定补贴,生产者随行就市出售玉米和大豆,形成购销主体多元化和多渠道流通的市场格局。
与玉米、大豆不同的是,稻谷作为口粮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则更需慎重前行。
“不能立马取消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在调研过程中,大部分政府官员、粮食种植者等持有同样的看法。他们担忧,在粮食市场体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一旦最低价格政策停止实施,势必引起粮食市场震荡,造成粮食价格陡降、农民收入下滑、种粮大户亏损,甚至出现大面积抛荒,危及粮食安全。
刘益平建议,为现行的最低收购价设置过渡期,并在过渡期内选择一个水稻主产省或若干个重点县,参照东北大豆的目标价格和东北玉米的 “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政策进行试点。
如何推进下一步改革,调研过程中,各方还提供了诸多建议:依靠大数据平台,科学下达粮食轮换,腾仓集并计划;探索从保产量向保产能转变,处理好国家“粮袋子”和农民“钱袋子”的关系;引导农字号金融机构真正回归农家,激活农村生产力发展;做好土地经营权这篇文章,释放耕地、林地、宅基地和建设用地的活力……
若今后对稻谷实行“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政策,那么补给谁?如何补?
有的认为应该补给种植水稻的新型经营主体;有的觉得应该按照实际播种面积发放补贴;有的建议,对农民的补贴应逐步向增强基本社会保障为主……
尽管这项改革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利益主体多元,但各方共识是“大家都不吃亏,才能往前走”。陈锡文说,下一步改革要做到利益平衡,让各方满意,才能推进农业进一步发展,确保粮食安全,确保种粮农户的收入稳定。

9月13日,山东聊城市茌平县金香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村民在收获成熟的谷子。
(CNS图)